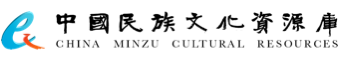

曾丽将博物馆的展览命名为“无字天书”。
记者:都说苗族服装是“穿在身上的史书”,您对这句话有什么体会?
曾丽:随着对苗族服装的研习,我发现没有一件苗族服装是一模一样的,但它们又是神似的。那是因为,绣什么是老祖宗规定好的。躲在大山深处的苗女,因为对祖先的敬仰和崇拜,耗上四五年的时间绣制一件精美绝伦的盛装,盛装上的纹样是他们的文化符号,是他们的祖先敬仰。我的父亲说过,在商品经济还没有进入苗寨的时候,苗衣上的记录才是真正的苗族原生态信息。苗族没有文字,苗衣上的刺绣传承了苗族的历史,因此确实可以说苗族服装是“穿在身上的史书”。
记者:听闻您这些年在贵阳和北京都开设了苗绣课堂,主要讲授什么内容?
曾丽:几年前,我重走了父亲走过的100个村寨。而我这次看到的和父亲以前看到的不再是同一种情景。在许多苗寨,大部分年轻人已经出去打工,只有很少的苗族绣娘还在一针一线地刺绣,用绣品换回车子、房子、娃儿读书的钱。尽管如此,很多苗族人已经不知道这些图样背后的意义了。
我想,一个东西不被需要的话就注定会消亡。怎样才能被需要?于是,我开设了苗绣课堂,让他们先读懂苗绣。我的上课方式是我和苗绣传承人共同站在讲台上。我想传达的就是,苗族人自己才是他们文化的主人,他们应该被尊重,并且应该了解到自己文化的意义和其中的智慧,进而鼓励他们回归家乡,从事自己的文化产品生产。
记者:请您简单介绍一下,苗绣与其他刺绣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?
曾丽:苗绣纹样和符号背后蕴藏着人类远古的文化因子,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,但现在却有很多本不属于苗族的纹样出现在所谓的“苗绣”上。
我曾和父亲一起研究,后来专门读人类学相关著作才渐渐明白,苗绣纹样复杂如宇宙,是不可以被随意拆解的。苗绣的形态和其他刺绣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常说的四大名绣,它们的工艺要求往往是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、追求写实,刺绣的内容大都是现实生活中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,比如猫、狗、金鱼等。但苗绣和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体系,它和现实生活完全没有关系。
记者:您觉得自己身上的文化责任是什么?
曾丽:文化是具有穿透性的。我要把一些珍贵的东西留下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不仅仅要帮助绣娘把绣片用合理的价格卖出去。我要面对的,不是一些刺绣的技巧,而是一种哲学:苗绣展现的是苗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,它是苗家人对天地、宇宙万物的认识,是万物关系,是基本的哲理和规则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认为苗家人对世界的认识更接近宇宙的本真状态。如果你能读懂苗绣中的符号的话,就能感受到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你、影响着你,它能把你带到它的那个世界里面去。
记者:请您具体解释一下您之前提到的“传统与现代相结合”是什么含义?
曾丽:现在,我国进入了新时代。相比父亲“用脚跑出来”的研究,新时代赋予我更多的机会,给了我更大的舞台,让我拥有更多元的媒介手段,把苗绣的故事讲得更生动。我不能让非遗文化精品被孤独地收藏着,必须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相结合,与现代和商业相融合,让非遗文化精品站到国际前沿。
记者:您的品牌“苗疆故事”的品牌定位和产品定位是什么?
曾丽:“苗疆故事”从品牌定位到产品定位都在强调我的原则:第一,尊重原有的文化;第二,用极致的态度来做卓越的产品。在苗族原本的生活里,一个妇女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绣出一套衣装,这本身就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。她们希望自己所做的事,不求速度,也不追求规模效应,只要做到最完美。
(本版图片均由曾丽提供)
来源:中国民族报